【白宫】美国的故事(四):邦克山之战

讲述人:《美国之春》作者,沃尔特·R·博恩曼(Walter R. Borneman)
1775年之春,距今250年,是一个可能向任一方倾斜的脆弱临界点。在列克星敦与康科德的短兵相接之后,马萨诸塞州开始担心自己会否孤军奋战。其立法机关向第二届大陆会议请愿,请求组建一支全国性质的军队。“既然各殖民地所集之军旨在共同保卫美洲之权利,谨请贵会承担其规制与统摄之责。” 这一步大胆地把十三殖民地推向合而为一的“国家政府”。
在等待答复期间,马萨诸塞州任命曾参加法印战争的老兵阿特马斯·沃德(Artemas Ward),指挥日益壮大的波士顿包围部队。这支松散的部队辖有多支团:马萨诸塞的威廉·普雷斯科特、康涅狄格的以色列·普特南,以及新罕布什尔的约翰·史塔克所部。由于缺乏完备的指挥体系,决策常靠“众议而定”,有时干脆凭个人威望拍板。是否占领查尔斯镇半岛上如匕首般直指英军占领之波士顿的邦克山,正是如此决定的。谁控制此高地,谁就掌控波士顿;然而数周来双方均未据守。
最终,英军总司令汤马士·盖奇将军(Thomas Gage,)决定采取行动。英方计划先夺取南侧的多切斯特高地,再转而攻击邦克山。进攻多切斯特定于6月18日早晨,至于期间沃德部会如何行动,英军并未太在意。在预定进攻前的两天里,应普雷斯科特与普特南催促,沃德同意加固查尔斯镇半岛及其约110英尺高的邦克山高点。渴望与英军决战的普特南主张把主防御工事修在更靠近波士顿、略低一些的小丘上,后被称作布里德山(邦克山战役,亦称布里德山战役)。
起义军方面,沃德麾下与其说是“军队”,不如说是一群松散的义勇队;用当时人们的话说,他们“为此大义坚韧不拔”。很少人穿着制服,大多数都穿着日常工装。人人肩上扛的,都是自家带来的火枪,只是有些枪比扛它们的人还老,几乎无人配刺刀。他们在布里德山上匆匆挖出的土垒不大,约130英尺见方。其要害在于北坡平缓直落米斯蒂克河畔,易为敌军顺势绕袭、切断阵地。
6月17日早晨,英军发现起义军阵地,盖奇遂延后多切斯特行动,转而加速攻击邦克山。查尔斯河上的皇家海军军舰与波士顿科普斯山上的炮位,一齐猛轰起义军新筑的工事。盖奇随即威廉·豪(William Howell)将军当天下午即刻发动进攻。盖奇在科普斯山上观战,他把望远镜递给寻求庇护于波士顿的保皇派阿比贾·威拉德,问他可认出叛军中谁在指挥。威拉德认出了威廉·普雷斯科特——殖民地战争时期的同袍,也是他的连襟。 “他会打吗?”盖奇追问。 “我不敢替他的士兵担保,”威拉德答道,“但普雷斯科特本人会一路打到地狱之门。”传奇由此展开。
豪命令1500人渡过查尔斯河。他们在邦克山下的海滩上毫无阻拦地登岸。因火药短缺,普雷斯科特的士兵在战壕中按兵不动,静观其变。豪将部队列阵于距内陆约一百码的高地,然而接下来的景象令他迟疑。约四百人的约翰·斯塔克上校(John Stark)新罕布什尔第一团已在米斯蒂克河滩的栅栏与匆筑的石障后布防,稳住了普雷斯科特那一线薄弱的左翼。见起义军集结,豪随即索要援军。等增援抵达时,他场上已有约二千二百人,而附近起义军大概只有其一半兵力。一度,人们清晰地意识到:此战与列克星敦的那场偶遇天差地别,这已不能称作遭遇战。1775年6月17日傍晚,当豪将军的部队向普雷斯科特与斯塔克的阵地推进时,任谁都看得出:一场硬仗在所难免。
英军分作两条长列上坡推进,直逼斯塔克阵地;美军主线肃然无声,深知火药有限。“稳住,别开火。”军官们反复叮嘱。与邦克山之战最常联系在一起的口令是:“等看到他们眼白再开火。”究竟谁说的?或许是威廉·普雷斯科特;其被重复的次数,也已不可考。亦有说法称,约翰·斯塔克在石障后告诫部属:看见敌人白色绑腿再打。豪的正规军继续压上。至约五十码处,一声“开火!”响起,起义军整线轰然怒吼。英军踉跄顿挫,队形大乱,且战且退。豪令其重整,再次前推。
后来的纸上谈兵者多指责豪让士兵直扑邦克山之举。但此等正面冲击并非豪的初衷。他原寄望于轻步兵从起义军左端抄插,沿线搅乱。继而由重装掷弹兵连列阵上刺刀,如推土机般强行贯穿。十一个轻步兵连、约三百五十人,以四人纵列猛冲石障;斯塔克的新罕布什尔兵则三列并肩而立。守军第一轮齐射,便重创来犯纵队。后续连队接替上前,也不过推进数码,便再被密集枪火撕裂。英军步兵艰难前挪,而新罕布什尔小伙子们稳如花岗岩。坡上掷弹兵连只闻枪声如雷,不见其果。豪确欲使掷弹兵扫穿起义军防线,旋即绕至壕后。然轻步兵既溃,掷弹兵亦为密集火力所遏。
第二次攻击亦告失败后,豪下令第三次冲击,直捣土方工事。此时起义军火药已危殆见底,不少人退向更高的邦克山顶。普雷斯科特手中仅余约一百五十人。终结抵抗的,并非勇气不足,亦非英军意志势不可挡,而是火药的短缺。剩余守军倒在英军刺刀之下。入夜,查尔斯镇半岛为英方所控;起义军则边打边撤,另筑防线。英军阵中弥漫着茫然与难以置信。山坡上满布殒命与垂亡者的红军服。豪将军不愿承认现实,他是赢了战场,却付出惊人的代价。 正如同僚亨利·克林顿(Bunker Hill)所评:“邦克山之战是一场代价高昂的胜利;再有一次,我们便完了。”
邦克山之后,毫无疑问,这已是全面战争。有人认为邦克山的军事重要性被夸大。然美国史长期颂扬此役,公众给予它与约克镇、阿拉莫、珍珠港同等敬意。若仅以战场控制权而论,邦克山战役是英军的一场胜利。但对1775年的起义军心气而言,此战极大鼓舞了士气。作为起义军与英军正规部队的首次大战,邦克山证明:那些日益自称为“美国人”的人有能力与英军抗衡、不落下风。
美国革命并非始于邦克山,更非终于邦克山。但邦克山之战证明,争取美国独立并缔造新国家的斗争,确实始于1775年的“美国之春”。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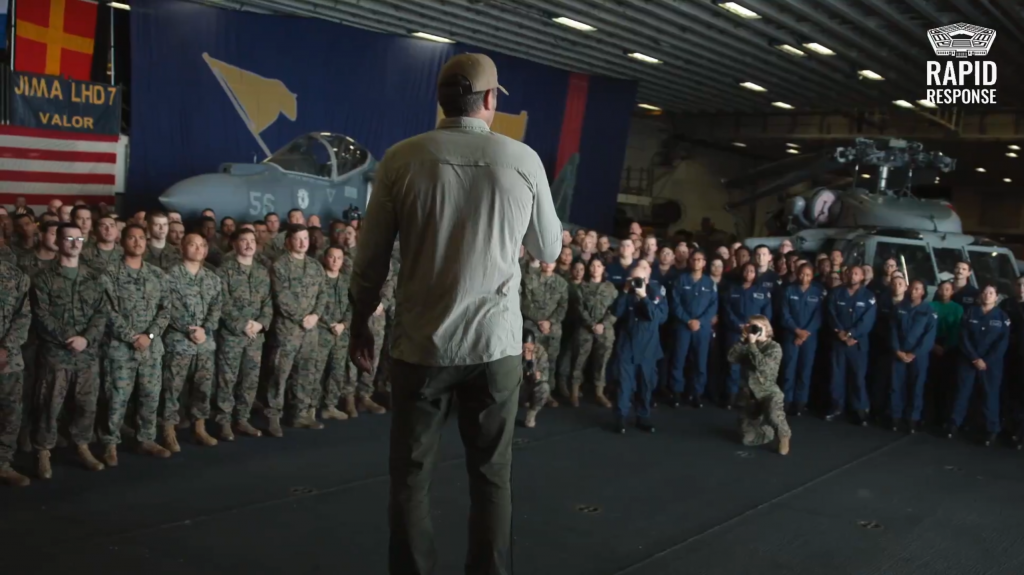



Responses